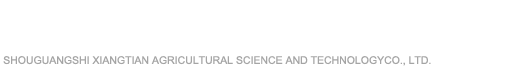九游会:他是黄埔一期身世的将领更是老蒋同乡为何挑选在大陆运营农场
来源:九游会 发布时间:2025-12-23 22:50:23
j9九游会:
这地儿其时但是热闹非凡,侵华日军正式签字屈服,哪怕是现在回看老照片,都能感到那种溢出屏幕的狂喜。
在那张挤满了大角色的现场合影里,你要是拿放大镜细心找,能在第七排那个不起眼的旮旯,揪出一个瘦得跟竹竿似的中将。
周围那帮同僚,一个个红光满面,正唾沫横飞地评论接下往来不断哪当“接纳大员”捞油水,要么便是盘算着怎样在整编里弄个实权军长当当。
可这位中将倒好,脑子里竟然冒出个极端离谱的想法:“这下好了,总算能回去服侍那些桃树了。”
没人能猜到,这个在国家高光时间专心只想“提桶跑路”的怪人,竟然是蒋介石的奉化嫡派老乡、黄埔一期的“天子门生”郑坡。
更没人敢信,就在短短一年前,正是这个满脑子只要庄稼的男人,带着一帮由逃亡学生和马帮凑成的“草台班子”,在怒江边上硬生生扛住了日军最疯狗般的反扑,保住了大西南最终的命根子。

1924年他背着个破帆布包进黄埔军校时,档案上的原籍就引来很多异常的眼光,乃至有人在背面嚼舌根,说他是走了后门进来的。

这个心气儿极高的年轻人其时只回了一句:“走后门的人,不需要清晨四点起来跑操。”
蒋介石一边忙着打内战,一边还要剿共,一道道加急调令发到郑坡手里,让他带兵去围歼江西。
这时分已经是旅长的郑坡,刚经历过“九一八”事故的影响,亲眼见过学生们咬破手指写的。
他站在杭州江干的防地上,看着手底下那些脸上稚气还没退洁净的新兵蛋子,心里那道坎怎样也过不去。
在他看来,武士的枪口对外那是不移至理,但若是要把这些好好的我国娃送去填内战的沟壑,这官不妥也罢。

所以,一件让整个南京国民政府都炸锅的事发生了:一位前途无量的黄埔系少将,直接把辞呈拍在了桌子上,跑到上海闸北买了一千亩地,真的办起了“大华农场”。
在那个我们都削尖了脑袋往权利中心钻、恨不得把头皮都挤破的时代,郑坡却脱下将校呢大衣,换上粗布短衫,蹲在田埂上研讨起了怎样改进水蜜桃。
假如不是后来日本人的刺刀逼到了家门口,我国历史上或许真的会多一位出色的农学家,而少一位抗日名将。

当他看到旧日的老部下、第87师和88师的兄弟们像割麦子相同倒在日军的机枪下时,那个熟睡的武士魂儿醒了。
但是,当他满腔热血跑到南京请战时,得到的却是一个冷冰冰的“闲差”——后方勤务部兵站。
在陈布雷传达这个录用时,那表情多少带着点看笑话的意味,毕竞关于一个正牌黄埔一期生来说,管后勤那是“伙夫头”干的事,丢人。

这五年里,他就像个隐形人,没人记住在这个苦逼的后勤岗位上还蹲着一尊大佛。
直到1942年,远征军在缅甸兵败如山倒,声称铜墙铁壁的防地被日军像撕纸相同容易撕碎,大批美援军械眼看就要落入敌手。
他环顾四周,那些素日里喊标语震天响的心腹们要么早就跑没影了,要么乱成了一锅粥。

其时的滇缅公路上,到处是没魂的溃兵和哭喊的难民,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就在后边追,间隔有时分都不到几公里。
他把路旁边的散兵游勇收拢起来,编成一个暂时的战役团断后;货车不行,就去雇马帮,乃至用牛拉;实在运不走的军械,哪怕是一颗子弹,也绝不留给日本人,通通炸掉。
最惊险的一幕发生在怒江惠通桥,他带着这支凑集起来的“乞丐部队”,硬是顶住了日军主力部队整整四十个昼夜的狂轰滥炸。
战后清点,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:郑坡抢运回来的物资,满足三个主力师打整整三个月;更要命的是,他抢回来的航空燃油,保住了昆明飞虎队的命根子。
假如没有这些油,陈纳德的那些飞机就只能趴在窝里当废铁,大西南的制空权早就没了。

到了1944年,当大反扑的号角吹响时,这位“救火队员”又干了一件让人张口结舌的事。
上面给了他一个“游击区总指挥”的空头衔,听着挺唬人,其实一分钱军饷没给。
换做他人早就不干了,或许直接躺平,可郑坡二话不说,把自己上海农场的股票全卖了,自掏腰包招兵买马。
在大理,他办起了一个独特的训练班,把美国联络官、傣族土司、逃亡大学生摁在一个锅里吃饭。
也便是在那个5月,他带着两千人翻越海拔四千米的雪山,靠吃竹根、喝雪水,奇迹般地迂回占领片马,一举捅开了腾冲日军的侧翼。

但是,便是这样一位立下赫赫战功的“国士”,在抗战成功后,当他人忙着“五子登科”(抢金子、房子、车子、票子、女子)时,他却再次递交了辞呈,理由是“旧伤复发”。
郑坡站在己经克复的农场田埂上,看着刚长出来的庄稼,淡淡地回了一句:“我要是图那个中委,当年就不会回来种田了。”
当人们戏弄他“将军种田,大材小用”时,这位前半生拿枪、后半生拿锄头的白叟说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:“将军能保国,农人能饱肚,谁大谁小?”

白日,他在大堤上挑土筑路,那是真出大力气;晚上,他躲在暗淡的油灯下编写《我国林木史话》。
为了保存这些宝贵的手稿,他把写好的纸张用油纸一层层包好,塞进拖拉机的坐垫里,生怕被人发现毁了。
纵观郑坡的终身,他好像总是在“错位”:该当官的时分他去种田,该享乐的时分他去拼命。
他不在乎头顶的帽子是钢盔仍是草帽,他在乎的,是脚下这片土地,究竟是完好的,仍是破碎的;这片土地上的公民,究竟是在流血,仍是在耕耘。

他走的时分很安静,除了那个藏满手稿的旧坐垫和一把磨得发亮的锄头,身外之物,一无所有。